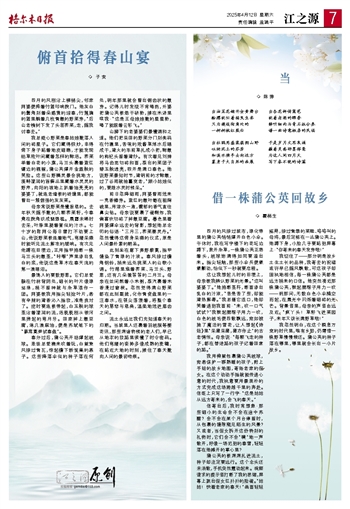◇ 瞿杨生
四月的风掠过城市,绿化带里的蒲公英悄悄撑开白色小伞。午休时,我在写字楼下的花坛边蹲下,拨开杂草,一株蒲公英正昂着头,绒球饱满得如同要溢出来。指尖轻触,那些小伞兵便簌簌颤动,恰似下一秒就要启程。
这让我想起儿时的田埂上,母亲教我辨认野菜的光景。“这叫婆婆丁。”她掐断茎秆,断面渗出乳白的汁液,“苦是苦了些,却能清热解毒。”我总嫌它涩口,她却笑着递到我面前:“来,吹一口气试试?”我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吹,白色的绒毛便四散飘远,宛如被施了魔法的雪花,让人想起《诗经》里“采薇采薇,薇亦作止”的古老惆怅。母亲说:“每颗飞走的种子,都在替迷路的孩子记着回家的路。”
我用棉絮包裹蒲公英绒球,宛若保护一群熟睡的孩子,附上手绘的故乡地图,寄给老家的侄女。在这个动动手指就能传递心意的时代,我执意要用最质朴的方式完成这场跨越千里的奔赴。信纸上只写了一行字:“这是姑姑从远方寄来的,会飞的春天。”
信寄出后,我时常想象:那些细小的生命会不会在途中苏醒?会不会在某个月台停留时,从包裹的缝隙窥见陌生的风景?又或者,当侄女拆开这份特别的礼物时,它们会不会“噗”地一声散开,好像一场迟到的春雪,轻轻落在她摊开的掌心里?
蒲公英的根深深扎进泥土,种子却注定要远行。这个念头还未消散,手机突然震动起来。视频请求的提示音打断了我的思绪,屏幕上跳出侄女红扑扑的脸蛋。“姑姑!快看老家的春天!”画面轻轻摇晃,掠过青翠的菜畦、咯咯叫的母鸡,最后定格在一丛蒲公英上。她蹲下身,小脸几乎要贴到屏幕上:“你寄来的春天发芽啦!”
我怔住了——那分明是故乡土生土长的品种,我寄去的祝福或许早已随风飘散,可这孩子却固执地相信,每一株蒲公英都是远方捎来的口信。她突然凑近那株蒲公英,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吹——刹那间,无数白色小伞腾空而起,在晨光中闪烁着细碎的光芒。背景音里,母亲的声音由远及近:“疯丫头!草籽飞进菜园子,来年又该长满野草啦!”
我忽然明白,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,唯有乡愁,仍需借一株野草慢慢偿还。蒲公英的种子落在哪里,哪里就会长出一小片故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