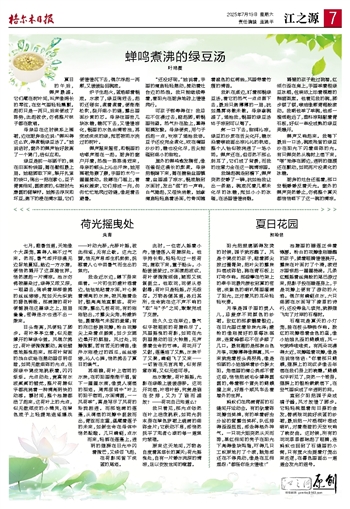叶艳霞
夏日的午后,蝉声最盛。它们藏在树叶间,叫声像绵长的琴弦,在空气里轻轻震颤。起初只是一两只,后来便成了阵势,此起彼伏,仿佛整片林子都在歌唱。
母亲总在这时候系上围裙,边往厨房走边说:“蝉叫得这么欢,得煮锅绿豆汤了。”她说话时,窗外的蝉声恰好拔高了一个调门,活似应和。
绿豆是前一年晒干的,装在旧面粉袋里,搁在橱柜最上层。她踮脚取下来,解开扎紧的袋口,倒出一把在掌心,豆子青黄相间,圆滚滚的,似被时光磨圆的翡翠籽。她拣去浮灰和坏豆,剩下的浸在清水里,它们便慢慢沉下去,偶尔浮起一两颗,又缓缓坠回碗底。
炉子生起火,蓝焰舔着锅底。水滚了,绿豆倒进去,起初还硬实,煮着煮着,便渐渐松软,裂开细小的缝,露出里面沙黄的芯。母亲往里丢几块冰糖,糖沉下去,又慢慢溶化,锅里的水色由清转浊,再变成淡淡的绿,宛若被雨水洗过的树叶。
蝉声越来越密,和锅里的咕嘟声混在一起。厨房的窗户开着,热浪一阵阵涌进来,母亲的额头上沁出汗珠,她用围裙角擦了擦,手里的木勺一圈圈搅动。我蹲在门槛上,看蚂蚁搬家,它们排成一列,匆匆忙忙地爬过砖缝,像赶着去避暑。
“还没好呢。”她说着,手里的蒲扇轻轻摆动,搅动着灶台边的热浪。我只能继续等着,看阳光在厨房地砖上慢慢爬行。
可孩子哪等得住?我总忍不住凑过去,踮起脚,朝锅里张望。热气扑在脸上,熏得眼睛发酸。母亲便笑,用勺子舀起一点,吹凉了递给我尝。豆子还没完全煮化,咬在嘴里沙沙的,糖也没化尽,舌尖能碰到细小的甜粒。
屋外的蝉鸣愈发稠密,像在催促这漫长的熬煮。母亲把锅端下来,搁在搪瓷盆里镇着,盆里盛了凉水,锅底触到水面时,发出“滋”的一声响,白气腾起,又很快消散。她拿蒲扇轻轻扇着汤面,竹骨间缠着褪色的红棉线,风里带着竹篾的清香。
我趴在桌边,盯着那锅绿豆汤,看它的热气一点点弱下去,最后只剩薄薄的一层,犹如晨雾将散未散。母亲拿碗盛了,递给我,锅里的绿豆汤终于凉到可以喝了。
第一口下去,甜润沁凉,绿豆的沙质在舌尖化开,糖水沿着喉咙画出凉沁沁的轨迹,整个人恰似被浇透了一场小雨。蝉声还在,但忽然不那么刺耳了,它们成了背景,而我的注意力全在这一碗清凉里。
我端起碗走到檐下,蝉声突然安静了一瞬,犹如给我让出一条路。碗底沉着几颗未化尽的冰糖,宛如小小的冰碴,在汤里慢慢消融。
隔壁的孩子跑过院墙,红领巾歪在肩上,手里举着根绿豆冰棍,包装纸上印着模糊的熊猫图案。他看见我的碗,脚步顿了顿,喉结像颗青梅般滚动。我朝他举了举碗,他却一溜烟跑远了,塑料凉鞋敲着青石板,好似一串没成熟的绿豆荚爆开。
蝉声又响起来。我喝下最后一口汤,碗底残留的绿豆沙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有只蝉突然从槐树上落下来,“嗒”地停在脚边,透明的翅膜还在颤动,如同两片没煮化的冰糖。
厨房的灶台还温着,那口空锅静静反着天光。窗外的蝉声突然静止,仿佛整个夏天都悄悄咽下了这一碗的清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