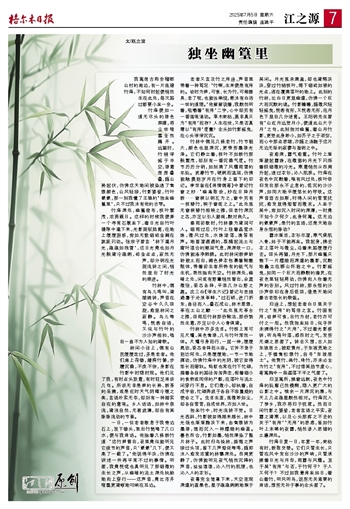文/赵立波
我寓居古称会稽郡山村的南边,有一片连绵竹海,不知何时起便悄然生在此处,每次路过都要小坐一会。
竹海便如一道无尽头的绿色屏障,将尘世喧嚣全然隔开。远望时,竹梢浮摇于半空,绿意层层叠叠,随山势起伏,仿佛这天地间被染透了青翠颜色,山风轻掠,竹影婆娑,竹叶簌簌,那一刻我懂了王维的“独坐幽篁里”,只不过我没有他的古琴。
竹海深处,幽篁密布,枝叶繁茂,浓荫蔽日。这样的时候我便择一个寻常石墩坐下,看日光自竹叶缝隙中漏下来,光影斑驳陆离,在地上缓缓游移,宛如无数细碎金屑在跳跃闪动。张宗子曾言:“林下漏月光,疏疏如残雪”,这日光竟也如月光般清冷疏朗,碎金点点,寂然无声,却分明在光斑流转之间,悄然显出了时光的痕迹。
竹林中,偶有鸟儿鸣叫,清脆婉转,声音在空谷中久久回旋,愈显林间之寂静。鸟儿啼鸣,恍若自语,又似与竹叶的沙沙声相和,唱出一曲不为人知的清歌。
林间小径上,偶有山民缓缓走过,多是老者。他们肩上荷锄,腰挎竹篓,步履沉稳,不疾不徐,身影在竹影中时隐时现。他们见了我,有时点头致意,有时驻足闲谈几句。所谈无非是笋的长势、新茶的采摘,或是近时天气阴晴冷暖之类,言语朴实无华,却别有一种踏实自在的意味。乡人话语,如林中泉流,清浅自然,无甚波澜,却自有其脉脉流动的节奏。
一日,一位老者歇息于我旁边石上,放下锄头,取出竹筒喝了几口水,便与我闲话。他指着几株新竹道:“这竹笋冒出,夜里竟似能听见它拔节的声音,只‘簌簌’几下,便又高了一截了。”他说得平淡,仿佛在讲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听罢,我竟恍惚也真听见了那细微的生长之声,从幽暗的泥土深处执拗地向上穿行——这声音,竟比市井喧嚣更清晰地叩响在耳边。
老者又言及竹之用途,声音里带着一种笃定:“竹啊,生来便是有用的。幼时为笋,可食;长为竹,可做器具;老了呢,也能当柴烧,断没有白活一世的道理。”他絮絮说着,我默然听着,咀嚼着“有用”二字,心中却另有一番滋味涌动。草木荣枯,莫非真只为“有用”而存?人生在世,又是否真需以“有用”度量?念头如竹影摇曳,在心头浮浮沉沉。
竹林中偶见几株老竹,竹节粗大,颜色也显深沉,更带些墨绿光泽。它们静立着,枝叶不如新竹那般繁茂,却别有一番沉稳气度。竹节历历分明,如刻满了风霜雨雪的年轮。抚摩竹节,硬朗而温润,仿佛能触摸到岁月在竹身上留下的印记。李笠翁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曾记竹窗之妙:“幽斋陈设,妙在日异月新……窗棂以明瓦为之,窗中另有一枝碧竹,映于窗纸之上。”此处虽无窗棂碧竹相映之雅,但老竹深沉之态,亦足以引人凝视,默对良久。
春雨初歇时,竹林最为清润可人。细雨过后,竹叶上挂着晶莹水珠,微风过处,水珠滚落,滴答有声。地面湿漉漉的,蒸腾起泥土与腐叶混合的潮润气息,深深吸一口,仿佛能涤净肺腑。此时林间新笋纷纷破土而出,褐色笋衣包裹着鲜嫩躯体,带着初生者所特有的锐气与生机,昂然指向天空。竹林深处,幽暗之处,间或有野蕈悄然冒出,伞盖微张,姿态各异,平添几分山野之趣。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曾记与芸娘避暑于沧浪亭畔,“过石桥,进门折东,曲径而入,叠石成山,林木葱翠,亭在土山之巅……”此处虽无亭台之雅,但雨后竹林那份鲜洁、那份勃然生意,亦足以令人心骨俱清。
竹林中亦多虫豸。竹枝上常可见尺蠖,其色青绿,几与竹叶浑然一体。尺蠖弓身而行,一屈一伸,缓缓爬动,姿态奇异而从容。它并不急于到达何处,只是缓缓地,一节一节地挪动,仿佛竹海中的光阴,被它拉得悠长而绵软。蚂蚁也常在竹下忙碌,循着各自的路径匆匆奔走,衔着细小的食物或同伴的尸骸,在落叶与泥土间穿行不息。它们微小,却执着,自成宇宙,忙碌奔波于各自不容置疑的使命之下。虫豸生涯,虽微渺如尘,却各自营营,自成世界,亦如人世。
独坐竹中,时光流转不觉。日光西斜,竹影被拉得越来越长,林中光线也渐渐黯淡下来,由青翠转为墨绿,继而沉入一种朦胧的幽蓝。暮色四合,竹影如墨,悄然浸染了整片林子。此时归鸟投林,振翅之声掠过头顶,留下几声短促啼鸣,随即没入愈发浓重的林霭深处。四周更静了,仿佛能听见夜气悄然沉降的声音,丝丝缕缕,沁入竹的肌理,也沁入人的衣衫。
夜幕完全笼罩下来,天空呈现深邃的蓝黑色,星子疏疏朗朗地缀于其间。月光虽未满盈,却也清辉淡淡,穿过竹梢枝叶,筛下细碎如银的光点,洒在覆满落叶的地上。此刻的竹林,比白日更显幽邃,仿佛一个巨大而沉默的谜。竹影幢幢,随微风轻轻摇曳,恍若有形,又恍若无形,在月色下显出几分迷离。王阳明先生曾有“山近月远觉月小,便道此山大于月”之句,此刻独对幽篁,看山月竹影,更觉此身渺小,如芥子之于须弥,而心中那点思绪,亦随之消融于这片无边无际的寂寥与澄明之中。
夜愈深,露气愈重。竹叶上渐渐凝起露珠,在微弱的月光下闪烁着极细微的冷光。寒意悄然从四周升起,透过衣衫,沁入肌肤。竹海在夜色中沉默着,唯有风过处,枝叶依旧发出那永不止息的、低沉的沙沙声,如同大地平缓悠长的呼吸。这声音亘古如斯,衬得人间的营营扰扰,愈发显得短暂而微末。人坐于其中,宛如沉入时间的深潭,一时竟不知今夕何夕,此身何属。这无边的簌簌声,是竹的言语,还是天地自身永恒的脉动?
露水渐浓,衣衫尽湿,寒气侵肌入骨,终于不能再坐。我起身,拂去衣上落叶与微尘,沿着来路缓缓行去。回头再望,月光下,那片幽篁只剩下一片朦胧而深邃的墨影,沉默地矗立在群山怀抱之中。竹影摇曳,如同一个巨大而静默的魂灵,在夜色里轻轻晃动,仿佛向人作着无声的告别。风过竹林,那永恒的沙沙声依旧在身后低回,像是天地间最古老悠长的歌谣。
归途上,想起老者白日里关于竹之“有用”的笃信之言。竹固有用,幼笋可食,壮竹为材,老竹亦可付之一炬。然我独坐终日,似乎并未探得竹之“大用”,不过看光影移转,听鸟鸣叶落,感四时之气,发些无端之思罢了。转念又想,古人如东坡居士,被贬黄州,于东坡荒地之上,手植青松翠竹,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他赏竹、画竹、咏竹,亦未必全为竹之“有用”,不过借其劲节虚心,寄寓胸中一段磊落不平之气罢了。
归至寓所,推窗远眺,夜色中竹海的轮廓已然模糊,隐入更广大的山影之中。惟余一片深沉的黑,与天上几点疏星默然相对。竹海沉入了梦乡,我亦将归于枕席。然而日间竹影之婆娑,老者言语之平实,夜露之清寒,以及心头那挥之不去的关于“有用”“无用”的思虑,皆如竹叶上未晞的夜露,悄然渗入思绪的土壤深处。
竹海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荣枯有时,新陈交替。它们只管生长,只管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,只管承接着日光与月华,雨露与风霜。至于其“有用”与否,于竹何干?于人又何干?不过如我辈闲坐终日,看山看竹,听风听鸟,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,想些无补于事的念头罢了。